
汉代彩绘木六博俑。
甘肃,地处黄河上游,雄踞陇山之侧,是丝绸之路的黄金通道,亦是东西方文明交融的千年走廊。日前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行的“墨韵文脉——甘肃丝路艺术珍品展”,汇聚敦煌研究院、甘肃省博物馆、甘肃简牍博物馆以及中国美术馆的240余件甘肃文物与艺术珍品,分为“书刻同辉”“绘塑同光”两个单元,溯源传统艺术的精神根脉,展现丝路文明的壮美气象。
书刻文化传承 凝聚艺术美感
展览“书刻同辉”单元集中呈现了殷商甲骨、汉简帛书、六朝写本、隋唐写经以及明肃府本《淳化阁帖》刻石等一系列文物珍品,生动勾勒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汉字与书法的发展脉络。
迄今为止,甘肃地区共出土简牍6万余枚,记录着两千多年前丝绸之路上的故事和历史文化演变,对研究丝绸之路、中国古代史和书法史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。在书体演变方面,简牍书法勾勒出由篆到隶、由隶到草的发展脉络。此次展览集中展示了居延新简、肩水金关汉简、敦煌马圈湾汉简、悬泉汉简及魏晋简牍等。居延新简中的篆书习字,既保留了篆书字形,又带有轻快的似隶书的笔意;肩水金关汉简的签牌上,隶书标志性的“蚕头燕尾”“一波三折”等纤毫毕现;《仪礼》木简、《相利善弊剑册》等隶书书风,无论是笔法、字法还是章法,都已十分成熟;敦煌悬泉汉简、马圈湾汉简中飘逸的长线、连绵的字势,简化和转变了隶书的规范与秩序,使线条带有强烈的草书韵律与节奏,彰显鲜活而率真的意味。
展厅的正中位置,陈列着15块明肃府本《淳化阁帖》刻石,这些刻石选用陕西富平县所产的富平石、历时7年刻成。《淳化阁帖》是宋太宗赵光义命提取内府秘阁珍藏的历代名家墨迹法书,由翰林侍书王著选辑摹刻、椎拓,以赐赠大臣用以学习书法的拓印本。这部丛帖多以“双钩填墨”的方式,力求精准还原103位书家、420件作品的真实笔迹、精妙笔法和生动笔势,对后世书法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,《淳化阁帖》原石已不存,其翻刻、重辑版本众多,品质良莠不齐。明肃府本《淳化阁帖》刻石“浓嫣遒劲,神彩泛溢”,品质上乘,价值极高。
此次从明肃府本《淳化阁帖》现存141块刻石中选展的15块,几乎都是经典的行草书。从张芝的龙蛇飞动、索靖的银钩虿尾、王羲之的中和遒逸、王献之的豪迈纵横,到欧阳询的劲险峭拔、虞世南的温润含蓄、褚遂良的疏朗绰约、柳公权的骨力瘦硬等,诠释着行草的灵动与生机,串联起刀锋、笔锋交融的书法图谱。
纵观汉字的产生与中国书法的发展史,从文字的滥觞到书体的定型,从实用的书写到审美的自觉,书法始终承载着历史的记忆,书刻着文化的传承,凝结着艺术的美感。
绘塑跨越时空 展示文化交融
展览“绘塑同光”单元展出了多位大家临摹敦煌壁画的作品,以及汉代木俑、魏晋画像砖、敦煌造像等,闪耀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美学精神,彰显着代代相传的艺术创造力。
20世纪以来,一批批艺术家走进敦煌,从壁画、彩塑中汲取营养,积累了大量的临摹和创作作品。其中,韩乐然1946年据莫高窟第257窟摹绘的油画作品《落发图》,与其另外两幅作品《听道图(乞食)》《成佛图》,重构了该窟的佛教故事叙事。莫高窟第257窟是北魏时期开凿的重要洞窟之一,其壁画内容和艺术风格反映了佛教艺术传入中国早期的特点,体现了西域与中原文化的融合。韩乐然的这三幅油画创作于抗战胜利后文化重建期,作品超越传统临摹的复制性,通过材质与形式的跨界实验,将敦煌艺术从洞窟的残片中剥离,重构为可流通、可凝视的现代经典,展现了东方宗教美学与西方绘画技法的深层对话。
敦煌石窟的塑像制作过程并不简单。首先,工匠们用圆木搭制塑像的骨架,用芨芨草或芦苇捆扎出人物的大体结构,然后敷泥进行塑造。粗泥塑造人物大样,细泥塑造人物表层、五官、配饰等细节。最后,再为塑像着色。展览中一尊北魏时期的持花菩萨立像,出土于敦煌莫高窟千相塔。菩萨立像为半浮雕形式,原为佛龛旁的胁侍菩萨,戴高冠,身材修长,面相方圆,眉目清秀,端庄娴静。头部以模具制,天衣和衣襞是后贴的,天衣、披巾和羊肠裙上的线条流畅,既有柔软贴体的质感,又富有装饰趣味。
敦煌莫高窟发现的木雕像大多属于唐宋时期,尤以盛唐为多。木雕像一般比同时期的泥塑像略小,但与同一时期洞窟内的木胎泥彩塑艺术风格统一。展品唐代佛倚坐木雕像造型比例协调,肌理和衣纹采用阴阳结合手法,细致入微,雕绘结合,生动华丽。佛像庄严慈悲,体现了盛唐时期造像“人物丰浓、肌胜于骨”的艺术风格,是莫高窟仅存的几件木雕佛像之一。
展览中,汉代木俑的古拙造型凝结着质朴的诗意,河西魏晋画像砖定格着市井烟火与生活温度,敦煌造像述说着中原与西域的文化交融……它们跨越时空,以多姿多彩的样态,展现出丝绸之路文化交融的艺术世界。
(编辑:吴艳)最新新闻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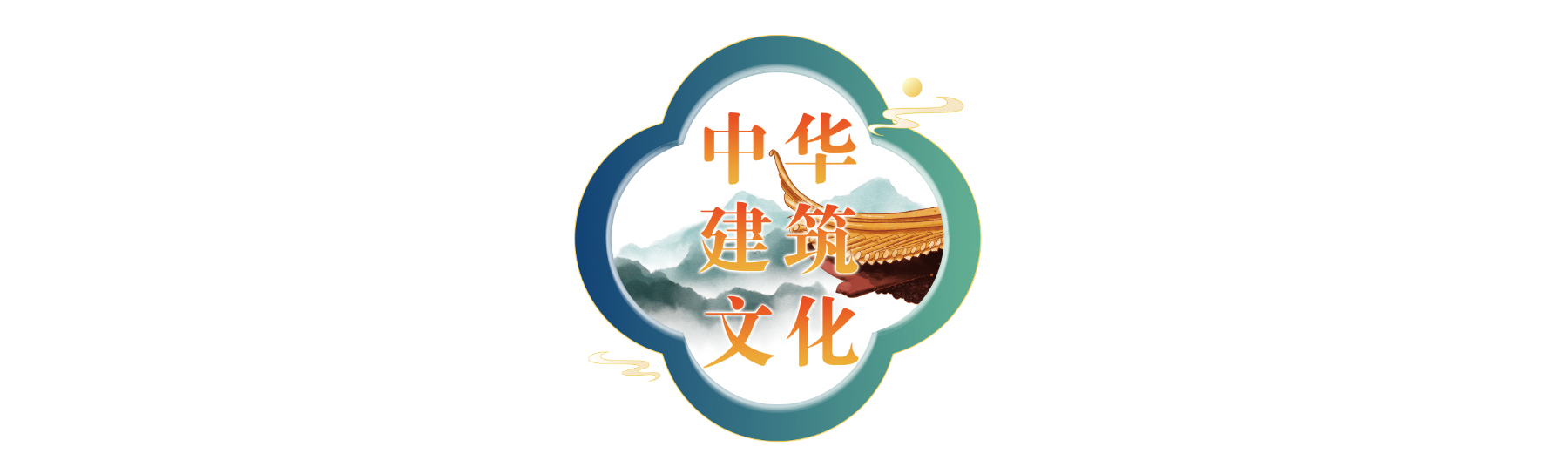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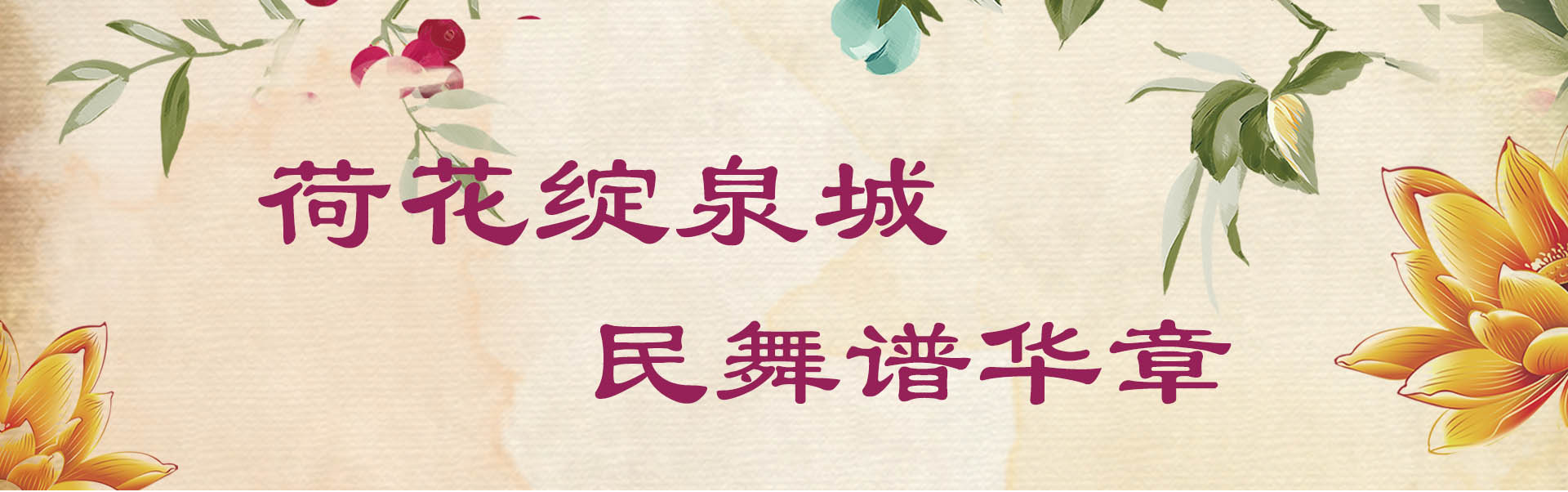
 zgmzzjw@sina.com
zgmzzjw@sina.com 